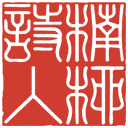旧年祖母身体愈好时,我们总是对那座山拥有着很强烈的感情,我在那座山上出生,我的完美童年在那里度过,有山有水,如今任然乐此不疲。
从山上举家迁下,也是为了我的学业而迫不得已,般下来后换过许多地方,住过恐怖的土房,旁边一两座孤坟,离村里的水泥路仍有一段路程。七八年前终于用一万多块买下别人的旧房,也算有了稳定的居所,至今还可以想起那时迁到“新房”的激动,父亲与我彻夜在房中打捉老鼠、争要房间。那年我大致十一二岁。
自读书时搬下来后,常常陪着祖母上山,或摘茶叶,或捡柴火,刚搬下来那几年,山上的田园仍在,还是会种下西瓜,土豆,地瓜;后来山上冷清,野猪逐渐变的猖狂,甚至那年上山与野猪遥遥相望,它也能淡定自若的摆头离去。山上种下的西瓜依旧是甘甜的,似乎是大山给了它一种独特的味道,旧年每至秋收时分,吵着闹着要祖母带我上山摘西瓜,几斤重的西瓜放在手机拿着下山,丝毫不感到辛苦。
以前家里也养过几只狗,小黄,小黑,我总是以它们的毛色命名,虽然不像别人家的让坐就坐,让躺就躺,也是很乖的,小黑自跟着我那天上学后,就不见了踪影,我还曾为此伤心过几年,和祖母上山时,它们总是会跟着一起上去的,现在看那山却也不高,但那时还是要中途歇上几回,偶尔走不动也向祖母撒撒娇,她总是让我和它们比赛,却也没有一次跑赢过的,它们会在前面转弯处停下,等你再次进入它们的视野,然后又消失在下一个转弯的路口。
也有意外,那一年我摘完西瓜喜极的蹦回山上老家,祖母远远的在后面扛着一篮子菜,够不到钥匙孔的我只能跳着开门,就是这回,幸运的被小黄咬了一口,咬在下巴上,或许它是想亲的,可能没算好我嘴的位置,祖母打它叫的声音仍旧尖锐刺耳,事后祖母也开玩笑的拿着“盲捶”给我揉一揉,这句老话我是听说过的,“狗咬了用盲锤揉一揉就好了”。
变化是从初中开始的,那一年刚搬到买来的新家,由于离家太远,家里只能让我选择寄宿,每每就只能一周回来一次了,与祖母一起上山的机会也少了许多,山上也不再种些瓜果,只还残种着一些水稻,或是油菜花。祖母身体亦不如从前,况且老人家又多怕些山上的孤魂野鬼找上,故也只是春季摘下头茶,陪她去菜园看看,喝喝老井里的水。走走歇歇,半晌午才到山下。
上一次祖母上山是什么时候已记不太清了,几年后祖父瘫痪,去年祖母更是患上青光眼,已经再也看不见那座山上的油菜花了。
那是祖母的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