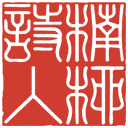断断续续的写了几个月,写了改,改了写,终还是含着眼泪将它写完,来记录二零一七年正月初七那天祖母与我、与家里的变化。
正月的初七,年已过了大半,父亲昨日便下去做事,我则等过元宵再做决定,可惜终究还是没能看到下雪,清晨透过窗望去只是白茫茫的一片片寒霜,泥草被裹上一层淡淡的白色。或许是少了从前堆雪人的伙伴,或许是未曾听见少年稚嫩的一声声“瑞雪兆丰年”的呐喊,掌管雪的仙女,青女,在这找不着乐趣,所幸到孩童多的地方去了罢。
在床上躺了半晌,天边开始有了颜色,仍不想起。
只听见祖父在叫祖母,“要煮早饭了呢。”
祖母自出嫁后,总不等天微亮便起来。家里务农的都赶早,以往叔公务农回来正好赶着早饭。今天直已到了六七点,饭该是好了,或是节里祖母忙的劳累,昨天晚睡了些。
好一会才听见祖母的声音,“怕是见了鬼罢,这埋人的火就是烧不燃…”想是祖母正在烧火,“平时没事,今天就是要翻精…”
祖母有时也这样骂,或是清早的柴火受了寒气,几次试着点不着,便骂那火坛子。祖母说那是鬼怪作祟,骂几句才能好了。
见祖母在柴房里骂的愈发急,叔公又早早的就往菜田里去了,祖父不能下地,我便忙着起来披了件棉衣,往柴房里去。
“怎么了?”我便看见祖母蹲坐在火堆的对边,身后的椅子斜摆着,火刚开始燃起来,祖母半弯着腰,一手提着要烧水的锅,一手去要去抓那吊钩。
“我来帮你。”我提起锅挂到钩上,缩到刚好的位置。
“这埋人的勾一擒擒不到,今天硬是见了鬼。”祖母眼神不好,又有高血压,近来早晨起来偶尔也说看不清东西,或是这两天天冷,该是祖母高血压带来的毛病,过两天应能好。
“我不蛮看见,你起来哒好,帮我发面,今天饭煮不赢了…”祖母往后寻着椅子坐下,误碰到我的手,一把握住,“手这么冷!”祖母顺着手摸到我披着的棉衣,“又不穿衣,一件袄还披着,快去穿衣。”
起的匆忙,也忘了冷,我只得应着,就去穿衣洗漱。
太阳悄悄的在后山升起,泥土开始露出它本来的模样,霜小了,却结出蒙蒙的一层雾,细腻的雾珠轻轻的结在手背上,眉头上,祖父也慢慢的起了床。
“作怪!几挂挂不到!”天已透亮,烧火房的灯还开着,面已煮好放在一边,祖母正提着沏壶想往吊钩上放,吊钩却是朝着另一边,祖母试过几次后心也急了。“今天不晓得么里怪事,这埋人的还看不见…”
我忙接过来挂好,祖母从口袋里拿出一叠折好的卫生纸,擦了擦眼睛,又塞回去。我这才仔细看祖母的眼睛,微闭着,眼角还悬着眼泪。
我试着在她眼前挥挥手,问她能不能看见,她眼神空泛着,只问我说什么。
我才意识到出了事。
叔公刚好回家,我连忙告诉他,他只不相信,进房来放下锄头,便往柴房去看看,先是在祖母面前晃了晃手,见祖母未说话,又晃一晃,祖母只是望着前面,或许是觉察到了风,只望着旁边问“谁来了?”
“真吗?真的看不见了哦!”叔公还不相信的问我。
“今天一早起来就看到细嗲摸沏壶,她这两天是说早上看不见。”我便想到早上的事。
“先吃饭,吃饭喊医师看看。”叔公再用手在祖母眼前晃了晃,祖母仍只是呆坐着。“这是不好了…”
祖父听到喊医师,也过来柴房,把轮椅摆正在祖母的面前,也挥挥手,什么话也没说,只呆望着祖母。
祖母却没能跟着祖父过上好日子,这些年来一直为家里劳碌,近年还要照料祖父的生活起居,如今日子刚好了些,又害了这病,怎不叫人怜惜。
我照着医师的号码打过去,约好应该是中午能过来一趟看看。
“噫,面精咸。”叔公盛好四碗面,端好一碗放到祖母手里,又端一碗给祖父。才吃了几口,说面放的太咸。
“她看不见啵。”祖父帮着解释。
那碗面,的确很咸,祖母只吃了几口,还是没说话。
锅里仍剩着小半碗的面,面汤在寒冷的天里结上厚厚的一层油,盆里胡乱堆着要洗的碗筷。祖父祖母仍就围坐在火堆边上。冷风吹透前面用油布钉着的窗,引来祖父的一阵咳嗽。
“你别动咯!”祖母或听到滚叫的热水,想去换下,用手试着去摸吊钩。
“你要烫到的!毛坨,你快来,水开了呢!”祖父一面唤我,祖母就已经蹲在了火堆边,一手握着吊钩,另一只手提起翻滚的沏壶想要放下,却怎么也放不平,因是火灶旁堆了柴火,旁边都是烧过的不平整的木炭,滚烫的开水从壶嘴里撒出来,溅到墙边正在打盹的懒猫身上,发出一阵阵撕裂的惨叫声,又泼到那火红的木炭上,滋滋地直冒烟。我忙接过还剩半壶的开水,扶着祖母坐下,幸而没烫伤她自己。
“开水你也去动,烫到怎么搞!”叔公听到滋火的声音也赶过来。
“看不见真不得了,什么做不得,看怎么得了…”我仍扶祖母坐下,祖母仍从兜里拿出那张叠好的卫生纸擦了擦眼睛,依旧放回去。又说如今大小事都不能做,不一会眼里又含满了泪水,我能感受到祖母的无助和孤单,直像个委屈的孩子。
祖母是个极要强的,祖父不能下地后都是由祖母细心照护,以前祖母总爱说祖父只知道坐着吃,也不问闲事。或是想到如今一下竟还不如了,不免又说了些怨天的话。
我一下没了主意,便回房里打电话给小姑妈,她听到消息,忙说等下就来,让我不要着急。我又打电话给父亲。
“喂,爸爸,细嗲看不见了…”
“么里呀?”父亲很诧异,又顿了顿,重新调整语气,“不会吧?”
“今天一早起来就看不见哒,满牙等下来,下午医师来了再看看。”我抽噎的说了些情况。
“嗯,好呢,等医师来看看,等医师来看看…”父亲没再说什么,只是应着,声音有些梗塞。
父亲本来想今天去城里的,祖母说初六是吉日,初七单日子出行不好,父亲便索性决定昨天一早走,祖母提前一天晚上熬好一大锅的茶叶蛋,一定要让父亲带着,昨天一早祖母便起来,一定要看着父亲上车。父亲走时仍旧戴着那顶带绒的平顶帽,穿着来时穿的胶鞋,挑着一副扁担,一边一个大袋子,有春夏天便要穿的衣物,还有祖母执意装好的腊肉、年货和几包生鸡蛋。母亲总说家里的东西要比外面好,每每让我们带些下去。一早上她在寒风里站了许久,直到听不见客车声。
这或许便是祖母眼里父亲最后的印象吧。
祖母平日里忙的紧,一下自然闲不住。我与父亲打电话时,她便摸着去床当头的角落里寻了根木拐杖。那拐杖原是几年前父亲在外带回来的,后来听父亲说过,其实是兰伯伯养老院里多出来的,父亲几年前带回来,祖母只以为是新买的,总说它好,雪天杵着不怕滑,样子又比家里上的木棍上得台面。这些年祖母健朗却用不到它,只堆放在这墙角里,祖母以前打趣着说等再老点就有用。不想今日,祖母想起它。
祖母仍放心不下几只鸡,硬要亲自去喂才好,我只得搀着她出去,祖母一手拿着拐杖,一手摸进袋子里抓一把谷子,边唤着、边洒在前面的路上,祖母的动作却比平日里迟疑了许多。祖母想去鸡笼看看,我仔细搀着,她仍旧不敢放开了脚步,家门前的路旁有条小河,祖母只靠着山走,我想拉着她到宽阔的路中间,她直拽住山边的草,曲卷着身体蹲坐下来,硬不肯挪步,说那边是河,要掉下去。
那一刻我感受到自己的心在被拉扯,在被撕碎。
等她的事情都安排妥当,终于才肯重新坐回到火堆边。
太阳已与往日一样缓缓升起,阳光随即洒在田间地头,空气中仍能闻到淡淡的草香,仿佛一切又重新开始。可那薄薄的一层雾却愈加的浓了,仍有很湿冷的寒气,透过窗,透过墙,侵入到这房里来。
不到晌午,小姑妈便赶了来,因她最小,又能常回来清洗祖父祖母的床单被褥,自然是祖母最喜爱的。父亲与我常年在外,难免依靠不住。
小姑妈才把车停好,就进来柴房里看过祖母,小心握住她的手问:“您晓得我是谁啵?”
“细山?细山来哒?”祖母就要往地上寻摸着拐杖,侧着头问。
“是哦。”小姑妈摆正旁边的椅子,挨着坐在祖母身边。“前天还来过,好好的,今天无里就看不见哒呢?”小姑妈又用拇指轻轻推起祖母的眼皮,才发现眼球已经浑浊,看不到自己的倒影。“呀,眼睛都浑了呢!”
“还有点亮吗?”小姑妈用手轻轻挥去祖母头发上的灰层,探着头望着祖母的微闭着的眼睛问。
“冒得亮。我又盐水洗哒,艾叶蒸哒,都不责业。”祖母又将刚寻摸到的拐杖重新放回到地上,只是呆望着前方。
“接了秀飞吗?又还冒来?”小姑妈侧过头来问我。
秀飞伯伯是村里仅有的医师,附近几个村里的、但凡大病小病都要他来看,早上给他打的电话时,他只说还在外地,一时赶不到家里,但仍尽量的往回赶。现已近中午,仍迟迟不见他来。
“他说还在别的地方,晚点才能来。”我回了小姑妈,转身又去给医师打电话。
“平时又没看这么忙。我先去把你姑妈接来,看看怎么办,等下也要煮饭,怕他来吃中饭,你看着细嗲,不要让她乱跑。”我应着,小姑妈先插上了饭,就骑车去接姑妈去了。
我又重新坐回到祖母身边,只拉着祖母的手,我也不说话,祖母也不说话,只是仍旧用纸擦着眼睛,我看向祖母的脸,眼泪就要止不住的往外流。
“细姨嗲怎么了?”岳奇从双扇门进来,看到祖母坐着不说话,端着椅子进来,问我。
“眼睛看不见哒。”我脸转过去朝着祖母,忙拿袖子擦去眼角上的泪珠。
“不会吧!”岳奇把椅子放在我旁边,又走到祖母后面,“细姨嗲!我是岳奇哦!”岳奇把手搭在祖母的手臂上,“岳奇啊?”祖母收起刚折好的卫生纸,侧着头循着声音问。“细姨嗲,你看得见吗?”岳奇用手在祖母眼前挥一挥,也看着祖母的脸。祖母似乎感受到了风,用手试着往前寻摸住岳奇的手,摸了摸,“岳奇哦。”又往上摸摸他穿多少衣服。“真的看不见了!”岳奇看着祖母的微闭着的眼睛,又转过头,疑惑的望着我,或是看到我脸上的泪痕,“胜林哥哥,你哭了啊?”想来他还没见过我哭的。“没。”我忙站起来往卧房里去拿纸擦干眼泪,岳奇仍再柴房又问了些祖母,就跑回家里去。
“莫乱说嘞。”不一会,便听到岳奇叫了姨祖母来,已到了屋外。“胜林哥哥都哭了。”岳奇小声的跟姨祖母说刚才是事,怕姨祖母不相信。
我也往柴房里去。
“怎么了?真吗看不见了?”姨祖母坐在祖母身边,轻轻用手推开祖母微闭着的眼皮,“一点亮都没有啊?”姨祖母问完祖母,然后侧着耳朵听。
“先是漆黑的,现在看都是白的。看不见东西。”祖母提着声音回道。
“姨嗲,喝茶。”我端了杯先前小姑妈泡好的茶过去,递给姨祖母,便就挨着姨祖母坐着。岳奇也端了椅子来坐到我旁边。
“看这是怎么说的好了?最是本分的人没落得好!偏生那些为非作歹的,活得好的奇。”姨祖母一面说,一面又宽慰着祖母,“磨了一世,怎么还该不得好下场。”又与祖母说了些陈年旧事,后又说起她们的八字。我听了些,便就去房里呆坐着。
直至中午,太阳照的人直发热,再看不到雾色,只有阳光与阴影。
姨祖母走后,祖母想去换件薄点的衣服,便拿起拐杖沿着墙摸过来。我忙搀扶着祖母到床沿上坐下。祖母换好衣服,从口袋里拿出那几叠折好的卫生纸放在一边,又往床头摸到一滚卫生纸,扯好一段,折了起来。
祖母买纸总是选便宜的买,是节省惯了的,村口铺子里的卫生纸有八块的、九块的、十块的。以前家里用的都是八块的纸,是很粗糙的厕纸。后来我上高中后,回家偶然发现自己房里都是放的十块的面巾纸,原是我曾责备过祖母说买的纸不好,但祖母自己房里仍旧用着八块的,直到现在也一样。
我忙去把那好一点的纸拿过来,偷偷的将那差的换了,祖母先是摸了摸,似发现这纸不一样,而后仍旧折起来。我告诉她不要用纸擦眼睛,不干净。或许祖母认为卫生纸也定要比她兜里那已有几年的方巾干净些,那方巾原是小姑妈买的,祖母很是爱惜,长期也洗的很干净,祖母只用它擦嘴,偶尔用它擦去衣服上残留的饭粒,平时也小心地收在里面夹衣的兜里。毕竟用了几年,仍旧免不得还是染上了谈谈的黑灰色的锅灰,也像她得手一样再洗不干净。
“天好,还要去把衣收下来挂着。”祖母才将折好的卫生纸放进口袋,又寻着棍要去楼上将衣服拿下来晒着。我想替祖母去,又怕以后我不在家她再摸不清路,遂搀扶着她一路上去,也当是让她走动走动。
祖母上楼很小心,顺着墙走在里面,旧房子的楼梯没装护栏,我试图将祖母拉出来些,祖母仍就靠着墙往上走,尽管衣服擦着墙发出沙沙的声音。
我将高处的衣服收下,祖母凭着记忆寻着篙子,拿了昨日里放的袜子和手巾,我收好衣服后拿起手机,录下那段记忆。我担心祖母以后再看不着我的样子,再难做着平日里容易的事情,又任由着眼泪哗啦啦的落下,顺着流到嘴角,滴在阳台上,溅起一层薄薄的尘灰。
即使我在祖母眼前如何哭泣,祖母也再看不见我的泪珠,再不能为我抹去脸颊上的泪水。
下楼时祖母仍走在里面,听见外面的车声,该是姑妈来了。
“妈。”姑妈在外便唤着祖母,寻着沙沙声进来,拍拍祖母手臂上的墙灰,又牵着祖母往柴房里去烤火。我接过祖母手里的袜子往外去挂起来。
“怎么好好的就看不见了呢?”姑妈又与祖母问了些情况,我凉完衣服,抹了抹眼泪才往房里走。
“先弄了饭吃,下午秀飞来了看看,中午应该是不来吃饭的。”说着姑妈就往厨房里忙了去,小姑妈趁着天气好将祖父祖母的衣服洗了,等叔公回来一齐吃过了饭,又商量起对策来。
“关个符试试?”姑妈又说是不是祖母碰了家里许久未动过的东西,或是在田里地里惹了不干净。
再说到原来屋旁边那座坟…
“不可能,那坟好久了,又不是新坟,骨头怕还有!”被坐在门口的叔公打断。
这房子原是买的,想到现在也有十二三年了,以前这房子右边是座小山丘,叔公想要建起来放些杂物,不想挖的时候里面却葬了座古坟,那时我还年幼,祖母不让我去看,我只偷瞄过几回,那坟还是石棺的,还能看到里面露出来的被子。后来叔公请了人择了吉日来迁走,又烧了香拜了,隔了许久才又动工加盖了现在右侧那间房。
“毛坨,拿刀来,跟我去砍两根竹子。”小姑妈想着还是关符试试,便唤着我去帮忙,姑妈也说去搬动下家里那些陈年旧物。
我随小姑妈往后山去,寻了几根大小齐整的小青竹砍下,拿回来后小姑妈又将这竹子应节砍成四段。
关符原是家里人生了怪疾时的办法,说像是镇压邪祟,旧年间我生水痘时家里也为我关过。需用青竹砍成四段,每段一个竹节,竹节两端一边长,一边短,节不能破,长的一端削尖,方便插进土里,再洗净后往短的一边放糯米,像是三粒几粒的也有讲究,我也不大记得住了,之后用红纸将短的一边包好,再拿细线紧紧捆住,最后用柴刀将这四节钉到房屋四角,至于钉几下,钉的时候的说辞,我便全然不晓得了。便说是在这之后,就能保家里病人痊愈。
我问祖母寻了些红纸来,再帮不上其他的忙了。小姑妈也不甚懂的,遂问了些姨祖母。姑妈又将右边那房里的东西再搬动了下,也过来帮忙。
直忙到下午两三点,医师方才来,连说节里往亲戚家去做了客,才误了不少时辰。这里看过后也要快走,哪里还有一家子在等他。小姑妈驳了他几句,怪他耽搁太久,定要仔细诊治。
医师看过后便说要打吊针,姑妈便搀着祖母躺去床上,祖母躺在床的外沿,小姑妈再寻了些棉毯垫在祖母腰后。医师又拨起眼皮再仔细看过,方说是青光眼,后又插了针,才回到偏房里来配药。见我们都退了回来,才小声的跟我们说:“以后怕是再看不见了。”
我控制不住眼泪,自己去柴房哭起来。
“青光眼几乎治不好,我也只能先帮着消炎。”医师边配药边说,“最好带她去市里看看。”
“是望伯伯不好吗?”授齐嗲看到屋外医师的车,应着声进来,小姑妈忙端了椅子,授齐嗲进来看到祖父坐在房里,又往祖母房里望了一眼:“呀,蒂娭怎么不好啊?”才接过小姑妈的椅子坐下,向姑妈问了些情况。
姨祖母也过来询问,小姑妈忙着去泡茶。
“去年我就看到她有半只眼睛浑了哩,和你们说了又都不在意!”授齐嗲接过小姑妈端来的茶,又说:“去年就跟蒂娭说要你们两个女带她去检查下,她也是说她一只眼睛看不见了,那时候治就强了。”
“治不好该怎么办呢?”姨祖母也接过茶,顺着椅子放在地上。
“万一治不好不还是只能要三哥回来。”小姑妈重新坐下。
“三婆要回来了,那就毛坨一个人在外攒钱了。”授齐嗲抿了一口茶,又说:“毛坨工资也高,也不要紧。”
“你爸爸要回来呀?”岳奇端了椅子来坐在我旁边,问我。
“毛坨,记得换药哦,我夜里再来。”医师刚说下午还有一家要紧着去看病,便只能嘱咐我来换药,有事再给他打电话。我应着,他便骑车去了。
我坐到祖母床沿上去,盯着药瓶,又看了看祖母的脸。这几年还是第一次这么仔细地看祖母,脸上早已经满是褶皱,渐露出和蔼慈祥的模样。
说起来前年我曾梦到祖母双目失明,梦里我才回家,祖母就要去衣柜当头摸着那挂着的袋子,说有好吃的留给我。祖母常在那里藏起我爱吃的零食,梦里的那一幕许久仍不能忘,至今难以释怀,醒来后我眼睛湿润,忙打电话给家里询问情况,叔公与父亲都只说一切皆好。
授齐嗲也说去年他在屋前看到祖母一只眼睛混了,让祖母遮住另一只眼睛看看,果然什么也看不见。后来祖母便与叔公和祖父说过,又寻了机会与小姑妈说。那时都不当回事,如今好的那只果然染病了,再来治如何来得及。
前两天我又听祖母说有几只鸡冠生的和别的不一样,冠是横着的,直到两天前我和姨祖母才偶然看到那两只鸡,原是鸡贩子装的眼遮,防止鸡直视斗架的。
这样看来祖母眼睛早有了预兆,确是我们的错了。
太阳落下门前的山间,一切又沉寂在黑暗里,泥土重新被裹上一层白色的寒霜,湿冷的空气从门缝里渗进来。我小心地盖好祖母插上针管的手,已经打了四五个吊瓶。房里昏暗起来,我按下床头的电灯开关,祖母眨了眨眼睛。
已是晚上七点多,在家从未这么晚吃过晚饭,屋前传来车的声音,该是医师回来了,药刚好还剩一点。
拔完针,我问祖母是否要吃点饭,祖母只抿着嘴,只不说话。我便用大碗盛了点饭,姑妈往里夹了菜,又泡上汤,才端给祖母。祖母沿着碗边往嘴里吃了些,汤顺着碗流到祖母手上,滴到衣服上,再滴到被子上,我赶紧用毛巾擦干,才看见祖母眼角的泪水,已经忍不住要流出。
“可能再看不见了。”医师仍在堂屋里吃饭,医师还是说:“最好去大医院看一看。”
“她又晕车。”小姑妈说。
祖母最坐不得车,我儿时随她一起坐车去往镇上的舅公家做客,刚下车她便说头昏的紧,又是吐又是恶心。最后只在舅公家坐了半晌,饭也没吃的便走回来了,至此后便什么车也不肯坐。
小姑妈最后说明天让姑爷们都来,一起商量着怎么办。
两个姑妈收拾完已经很晚才回去,跟祖母说明天上午一早就来,带她去市里看看,叫她放宽心。
今年初七的天黑的早,黑的什么也看不见。我摸索着走到外面,回想起祖母教我识字、教我颜色,又想到以后祖母的生活。
躺到床上我迟迟睡不着,那晚的夜出奇的黑,黑到看不清手指,黑到不知道方向,黑到不管睁着眼睛还是闭上眼睛都是黑夜。
第二天一大早天刚微微亮,姑妈和姑爷便都赶了来,还雇来一辆面包车,开始祖母一再的不愿意,姑妈最后还是将她裹在被子里,紧紧抱着,一同往市里去做检查。
我没去,只让我和表弟在家里等。那天等了许久,我已忘了那天中午谁煮的饭,干了些什么。或许我就一直坐在火堆旁边,就呆坐着。
祖母以前总说若不是晕车也想去市里看看,我总开玩笑带她走路去。自工作后,我也曾梦想过带着她和祖父一起去市里转转。也看看洞庭湖,看看岳阳楼,也看看城里的高楼大厦。
将近傍晚,他们才回来,姑妈仍抱着祖母下来。
父亲也回来了。
父亲的被子、衣物,还有他生日时我送的小电视,还有祖母塞给他的腊肉,都回来了。
祖母被确诊患上了青光眼。由于送医太晚,几乎没了治好的希望。
“蒂娭是个善良人,怎么能患上这病呢?”那天二叔公从家门前路过,问我家里缘故,又说:“天也是不开眼呀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