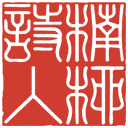已是夜里十点,刚与熟友闲逛回来,进门便躺在阳台的单人沙发上,迎面是一株海棠,懒懒的,也不开花,透过阳台往下望,街道上乌泱泱的一片,纷纷扰的人群,在这个夜晚也丝毫没有停歇。
刚怔住一会,隐约听见房间内的衣柜角落有轻轻的嗡嗡声响,走过去看,一只残了脚的幼蜂,不知在这扇了多久,正拖着残重身体四面的爬,正愁如何处理了它,不慎又跌落到一边的宣纸上,索性拿了笔,要送了它出去,它脚却失了力,也抓不住笔上的羊毛,好容易将它移了出去,只息在阳台的那一株海棠上。
桌上的电话响起,没有名字,过去接起。
“喂?”
“喂,毛坨,我是田芳哦。”田芳是桂英奶的孙女,该是比我大四五岁,前些年在广州工作,近年像是回到家里找了事做,个子不高,消瘦的很,听祖母说已有个不错的男人看上。我与她却不甚联系,上次给我电话或是说她眼睛有些问题,也不知如今怎样。
“哦,怎么了?什么事吗?”知道是她,我便问道。
“你有慧姐的联系方式罢?”她的声音不像上次那样忧伤哀沉,倒是急促了些。
“慧姐?老黑家慧姐姐吗?我有老黑的电话,有什么事吗?”我一时没听过来,且不敢确定她问的谁,或是老黑他家慧姐,姨祖母的孙女,也曾听说她在广州,只是家乡的同辈,我们男孩自顽在一块的,却与她们来往的少,自不敢认定。
“是的,她去深圳了,说去散散心。”她回道。
“也好啊,她现在深圳吗?”我却是去年春节才见过她的,如今时尚许多,生的便漂亮,那时听说她已有婚配,祖母说那男人如何能干结实,且说得怎般高挑稳重,早早拟定了婚期。不想今年国庆回去时,听闻叔公说起慧姐婚事却废了,那男人又是怎样做事行派,如何粗暴无礼,诸多种事,直废了婚事,慧姐怀了孩子,也只能做了。距今该有了三、四月,散心便是为此事了。
“我也不清楚,反正听她说一个人,也不熟悉路,和我说没有熟人。”她又停顿一会,接着说:“看你有没有空,去接下她。”
我却已打算洗漱便睡了,听到这,便且停住,问道:“你有她电话吗?我打个电话她问问。”又想起:“她晚上住在哪呢?”
“就是不知道她住哪,我先把电话发给你,你打电话问问,陪她找个地方先安顿好罢?”她愈发急了,又说:“她一个人也不熟悉,你多帮帮忙罢?”
我一一应着,挂断电话,收到她发来的电话号码,紧接着拨过去。
“喂?”电话刚响,便听到她的声音,听起来有些伤感脆弱,却不像她在家乡那般的甜美爽脆。
“喂,我是毛坨哦,你来深圳了吗?”我忙着问道。
原来她已到了几日,现住在朋友家,只叫我不要担心,又说她已不是孩子,自会照顾自己,待她在这稳定后,再来找我闲聚。我只得应着,又问了她住的地方,是否生活的好,让她有事便来找我。她也应着。
我对她的感慨,或是异乡遇到至亲的不易;或是她的经历种种令人怜惜;或是国庆节,偶见到的大伯眼角上的泪水与抽泣。
挂掉电话,已是近十二点,又不知在阳台坐了多久,往那一株海棠社看,夜里的海棠瘫着月色,竟露出一些冷傲与柔丽。那只息在叶上的幼蜂,却不知飞到哪去了。